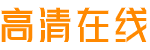每到周三的傍晚,明薇都會準時按下北京市順義區一戶高檔住宅的門鈴。8歲女孩文彥就藏在門后,接下來的三個小時,她們將一起做手工、復習功課,或者僅僅是在臥室里聊天。
在這個被稱為“家”的空間里,明薇的角色模糊而復雜——她是女孩家長付費聘請的老師,是陪玩的姐姐,有時,是不經意間被呼喚的“媽媽”。
在過去的一年里,明薇接觸過8個這樣的孩子。這些家庭有著相似的輪廓:父母事業繁忙,時間稀缺。家長們不僅希望陪讀老師能夠給孩子知識上的啟蒙,同時希望能填滿父母難以兼顧的時間。
在工作與家庭中艱難尋找平衡的家長們,將育兒“外包”給像明薇這樣的大學生。這些大學生陪著孩子做作業、讀繪本、學拼音、捉迷藏、出門玩耍,有時還需要在家中將孩子們哄睡。與注重課業輔導的家教不同,陪伴服務有更多情緒投入、更多情感交流。
而在家長們這邊,問題被暫時解決了,但大部分母親卻并未感到安慰。最好的育兒應該是親力親為的,有受訪者說,“我們做父母是失職的。”
▲2025年8月8日,山東青島,志愿者陪伴小朋友,緩解職工家庭“帶娃難”,豐富孩子們的暑期生活。圖源IC
“無痛當媽”
明薇與文彥的緣分始于2024年下半年。
彼時,明薇剛大學畢業不久,住在北京市順義區,暫時沒能找到工作。但很快她就發現,住在附近的家長們有不少育兒“外包”的需求:他們時間匱乏,渴望有人進入家庭承擔一部分父母的工作,陪伴孩子,“德智體美各方面都要培養一下。”
雖然明薇之前連家教都沒有做過,但早年間考了教師資格證,也喜歡孩子,看到那些在她輔導下被訂正的作業本會有成就感,自認“與孩子在一起的時光是治愈的”。
第一次面試時,文彥的母親開誠布公:她有自己的事業要忙,無法花太多時間陪孩子。明薇猜想,或許是自己展現出的語言表達能力、細致耐心的性格打動了對方,當然,還有她的外形——“她說想找個稍微好看一點的,因為誰帶孩子,以后孩子就長得像誰。”
工作很快確定了下來,具體內容是:每周三上門一次,一次3個小時。這位年輕的母親將明薇拉進一個工作群中——這個家庭里還有另外兩位家庭老師負責更具體的課業輔導。而明薇的主要職責是統籌性的工作,她需要根據學校教學內容制定計劃,承擔起家校溝通的橋梁,并對女孩的性格養成進行一定的引導。
第一次和文彥見面,女孩因為害羞而躲在桌子下不肯露面。明薇想起孩子母親的囑咐,將孩子培養得開朗一些,“至少見人要打招呼。”
在明薇看來,文彥膽怯,對人慢熱,甚至有些孤僻,常常自卑。這是明薇后來在一次次與文彥的相處中得出的結論。
她們會在周三傍晚一起做學校留下的手工作業,有時看女孩狀態不好,她會帶著女孩到附近走走。一個月后,女孩開始愿意向明薇吐露學校里的事。兩個人關系更親密后,明薇主動糾正了稱呼:起初孩子叫她“老師”,她讓孩子改為姐姐。
明薇很少再見到她的母親。每周上門前,孩子的媽媽會在群里發送學校當周的學習內容,也會將學校老師的反饋傳遞給她:“孩子最近可能有自己的想法,要多和她交流一下;孩子最近上課總是開小差,你問問孩子是怎么了。”
明薇會每周撰寫工作日志,記錄當周內容與孩子情況,但鮮少收到家長有信息量的回復,多半是一句:“辛苦老師,孩子這塊需要你費心。”
一次陪伴三小時收入僅三百元,但明薇不太在乎,“我很喜歡這個孩子,想要多陪陪她。”文彥羞用語言表達愛,但總會將學校里做的手工——黏土蛋糕、扭扭棒、手工本子——珍重地在她到來時展示。時不時地,文彥會輕輕牽住她的手。如果可以,明薇希望能陪伴文彥一輩子。
從去年年底至今,明薇接觸過8個孩子。這些家庭的父母無不以事業為重,孩子們也大多內向。即使她對每個孩子都付出了十足的耐心,內心深處卻始終縈繞著一個想法:如果是父母親自來帶,效果或許會更好。
▲社交媒體上,家長們在尋找陪讀服務,大學生們在尋找兼職。某社交平臺截圖
大學生帶娃
像明薇這類提供陪伴式服務的大學生,正成為大城市家庭教育生態中一個悄然興起的群體。
延影22歲,今年9月來到北京讀研后,她試著在社交平臺上找一份提供陪伴服務的兼職。她曾做過更注重課業輔導的家教,但她還是更傾向于陪伴服務:跟孩子玩耍更輕松,也有更多情感交流。
此前在東北某省一座邊境城市,她帶過一個四年級女孩。家長工作太忙,孩子一個人在家。她理解家長找她的原因:“大學生比育兒嫂素質高,性價比高。”
剛接這個單子時,孩子的母親并沒有制定嚴苛的學習計劃,“就是輔導作業,預習復習。” 延影從陪寫作業開始,之后兩人一起畫畫、玩耍。后來關系好了,延影發現,孩子會提前完成作業,只為和她多玩些時間。
到后來,母親已對課業不再多問。延影會主動發送當天作業情況,但不提及陪伴孩子玩耍。不過延影想,家長對這些都是清楚的。
她說東北人“看破不說破”:“她知道你帶著孩子玩,但不會明說,還是希望你以輔導為主,但實際上也愿意你陪著孩子玩。”
每天晚上,延影會從女孩的興趣班接她下課,之后在家中常常待到9點多鐘,將女孩哄睡。當她離開時,孩子的父母往往還沒到家,“孩子媽媽在家里裝有監控,有時候會看我們在家干什么。”
她幾乎與那個女孩度過了整整一年的課后時光。她們在夜晚的街道溜達,周末去游樂場玩耍。延影常覺得女孩“可憐”:“雖說家庭條件好,但父母沒辦法給她太多陪伴,她有很多想法沒人分享,只好跟我說。”
一年多來,延影只見過孩子媽媽兩次。這對做生意的父母工作繁忙,母親大多通過家中監控或孩子口中了解情況。
吳風23歲,在今年年初拿到研究生錄取通知后,就在家鄉華北某省省會城市找到一份接送孩子的工作。在這個準備升學的空當,她希望找一些輕松的兼職賺一些零花錢。熟人介紹,時薪80元,要求簡單:每天把孩子從學校接回,輔導作業,之后陪玩一會兒,不要讓孩子總看電視或手機。
吳風帶著這個一年級小女孩拼樂高、做手工、畫畫、玩游戲,在樓下跑跑跳跳。兩人后來關系親近,女孩會把學校里發的零食悄悄帶給吳風。
今年春天,在北京某高校讀書的蘋果接到一個幼升小的單子。一個打印店老板娘聯系她,希望為孩子制定幼升小學習計劃:讀繪本,認識簡單漢字,學習20以內加減法,掌握基本英語表達。
蘋果就在打印店一角開始教學工作。說是上課,但五歲多孩子并不能完全理解這個大姐姐為什么會出現在這里,“她以為是這個姐姐過來陪她,一起學點東西,大部分時候,我們還是在玩游戲。”